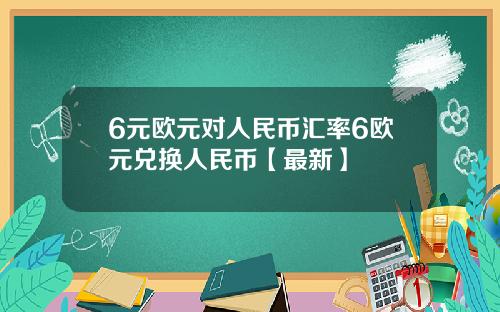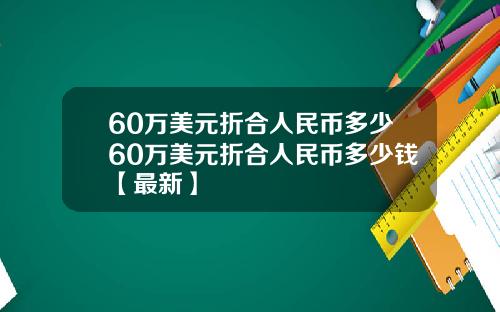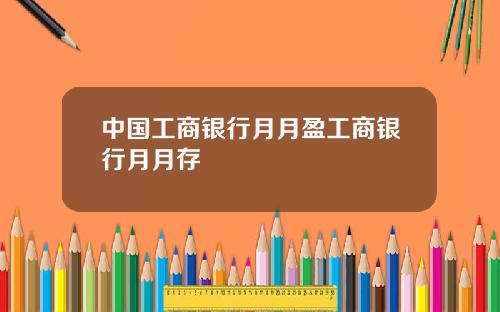本该是真善美的启蒙,如今却变成了儿童邪典。
作者:朱末
来源:快刀财经(ID:kuaidaocaijing)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人教版教材插图”事件发酵、登顶热搜后,一张“男童舔汗”的绘本插图再次引爆了舆论。
配图中,一个男孩边舔舐着女生的手臂,边说:“姐姐,你好漂亮,你的汗是什么味道呢?”另一个男生则回答道:“呃,也是咸咸的。”本是用于科普的桥段,变成了色情擦边球。
而它的背后,是号称“中国最好的绘本编辑团队”的《东方娃娃》,以及国内规模最大的出版产业集团凤凰传媒。《东方娃娃》杂志的订阅量通常都在百万起步,很多幼儿园都会当教材使用,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无独有偶,网友们还发现了许多其他“诡异”的童书插画。绘本《扁鹊治病》里,女性角色光胳膊搂抱着医生,名医扁鹊不仅格外“猥琐”,还没有身为医者的自知,一举一动充满轻浮。
而在另一本叫《挠痒痒》的绘本里,画的是满脸胡茬的男性亲吻儿童的臀部,让人生理性不适的同时,更是三观尽失。
本该是真善美的启蒙,如今却变成了儿童邪典,整个就是一出荒诞的魔幻现象。要知道,如今,中国的未成年读者已高达3.67亿人次,每年都有4万多种童书出版,印刷量高达8亿册,印刷数目全球第一,近年来销售额更是高达200亿人民币,俨然已成为童书出版大国。
孰能料到,无辜的儿童竟然成了灰色地带的“牺牲品”。成年人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但对形同白纸的儿童来说,将在潜移默化中直接影响人格和行为的塑造,内容可以整改,但已经造成的不良影响却难以挽回。
千言万语汇成鲁迅先生那句:救救孩子。
01
童书出版为何“失控”?
事实上,国内童书出版的发展史,已经超过70载。
1950年,新中国出版业刚刚拉开序幕,彼时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直到1952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成为首家专业少儿出版社,此后在1956年,中国共青团中央创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一南一北”的格局,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童书出版力量。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童书出版有了“质的飞越”。1977年至1988年,全国总计出版童书75553种,总印数83.03亿册,比1950年至1976年的出版数量,种数增长3.1倍,图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迎来了童书出版的“黄金时代”,随着家长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不仅跨入了世界少年儿童出版大国的行业,还开始向少儿出版强国迈进。
在2002年至2017年间,童书零售市场连续15年增幅超过10%。据当当网统计,2015年在当当网上售卖的童书达到1.5亿册,童书销售额占整体图书销售的30%左右。
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看似较低的进入门槛,让越来越多的图书出版社加入童书出版的行列,谁都想分一杯羹。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561家出版社中。有540家以上在出版童书,占比96%以上。童书出版数量增长20%,而其他图书增长率仅为10%,童书占据纸质版图书的头部地位。
竞争越来越激烈,蛋糕却只有那么大。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实现利润最大化,原本健康蓬勃的童书生意,开始变味、失控、疯狂,各种问题触目惊心。
——粗制滥造、出版内容良莠不齐。利益至上的出版商们,奉行“拿来主义”策略。国外有好的童书面市,不愿高价买版权,就拼拼凑凑、修修改改,换个名字,摇身一变为少儿“新读物”,导致盗版丛生、伪书泛滥。
2021年,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开展的“图书质量管理2021”专项工作中,共抽查了300多种图书,其中62种图书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不少正是2020年以来出版的少儿图书。
——资历欠缺,队伍配置力量有限。由于童书浅显易懂且篇幅较短,很多出版社为了开源节流,并不会聘请有经验的编辑和插画师,很多没毕业的实习生匆匆培训两天就开始上岗造书。
快消品盛行的销售法则,也让出版社难以沉下心来打磨原创书籍,一味沉迷于流量,更希望跟风于“爆书”。
还有出版社会邀请优秀作家合作,但由于这部分作家每年产量有限,新人又成长不够,出版社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名家挂名主编,其实图书质量并没有保证。
自媒体的盛行,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并不真正懂书的“网红达人”们,拿着写好的文案,反复给家长洗脑来刺激销量,大环境已然如此,能对童书提出建设性意见的空间几乎不存在。
——私人夹带,混浊整个行业风气。童话大王郑渊洁曾炮轰中国童书销售泡沫极大,甚至和不法行为有牵连,有些童书作者以讲课为名进入校园售书,郑渊洁还晒出了某小学校方的征订单。
▲图/郑渊洁微博
北京青年报也报道称,通过将图书作者带入校园演讲,来达到销售书籍的方式,早已成为不少图书从业者公认的“潜规则”。
种种乱象不过是冰山一角,失去了底线的童书,还在向深渊堕去。
02
谁在让童书变“毒书”?
出版社的尸位素餐,让劣质儿童出版物愈发猖獗。本该专业、纯净的童书市场,却充斥着暴力、色情、恐怖元素,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潜伏在孩子们身边。
如今,不少儿童图书柜台,公然摆放着如《尸画》《向日鬼呻吟》《教主,你就从了吧》等儿童不宜的书籍,封面与插图,均有着大量的骷髅、鬼脸、凶手等刺激性画面。
成年人以抽象思维为主,儿童却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稍有不慎的出格就会吸引他们。这样的画面过多出现在儿童读物上,只会让更多孩子将“不正常”视为常态。
除了插画问题,内容上的漏洞更是令人发指。层出不穷的“黑童话”,在近年来屡禁不止:丑小鸭没有变成天鹅,而是因为长得难看离家出走,最后变成了一盘烤鸭;美人鱼的故事中,公主变成了复仇女巫,邪恶至极。
在曾被点名过的《小熊过生日的绘本》里,许多动物朋友参加小熊的生日会,吃蛋糕时却有一位朋友不见了,餐桌上则多了只烤鸡。故事里不断用线索暗示,朋友变成了餐桌上的一道菜,细思极恐。
同样地,另一套《不要随便摸我》的整套绘本里,名义上打着安全教育知识的幌子,背地里却将某些行为动作描述得细致入微,十分露骨,其心可诛。
作为儿童价值导向的神圣标杆,大量的童书非但没有做出榜样作用,反而利用内容进行畸形引导,荼毒着涉世未深的儿童们。
还有更严重的,在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中,竟用大片文字描写了小孩的自杀心理和过程:“我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我纵身从教学楼跳了下去,教室的窗户一扇一扇从我身边掠过,我像一片树叶一般飘向大地。”
这并非个例。畅销童书《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之天真妈妈》里,也有关于自杀的描写:“栓根绳子在脖子上,再找一棵数吊死。从楼顶像鸟儿一样张开双臂飞下来……”童书里根本不该有的情节,却堂而皇之地发行了出来。
这些只是经过曝光的问题绘本,整个童书市场到底还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流传,没人知道答案。
中间并非没有过抗议。早在2013年,面对社会各界尤其是广大家长师生对劣质儿童出版物的强烈反映,中宣部、教育部等五部门就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相关提案中也提到了加强少儿出版物质量监控的提案。提案认为,出版不能只是出版界的事情,三审三校的标准不能形同虚设,也不能被查出才略施小惩,应设立专门监控举报热线。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有相关部门的出台意见是远远不够的,阳光无法高强度照射的地方,黑暗还会无限滋生。
03
问题童书影响有多恶劣?
在近几日的互联网上,对“问题”童书和教材的民意滔天,要求彻底清除行业弊病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
群情激愤中,却出现了一些“洗白”言论,诸如“仁者见仁、淫者见淫”“画风问题都要高举着大棒,喊打喊杀吗?”“资金不够,才导致粗制滥造,国人不必过分敏感”等。
诚然,艺术可以多元,可以自由,甚至可以离经叛道。但在儿童领域,必须要有明确的红线,必须零容忍。
前车之鉴依然历历在目。在中国香港地区,多个香港教材、图书存在篡改历史的问题,对“港独”观念大谈特谈,刻意放大“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导致3700多名学生因参与“黑暴”被捕,令亲者痛、爱者伤。
而在2021年,新疆发布了让人震惊的“毒教材”案件,原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带头编写“毒教材”,歪曲历史,给学生灌输分裂思想。
在沙塔尔·沙吾提的授意下,教育厅副厅长,出版社社长和编辑等若干人,专门挑选宣扬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思想内容,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目的。
这套从小学到高中的维语教材,从2003年开始,全区发行了2500万余册,时间长达13年,给整整一代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影响。
沙塔尔·沙吾提亲口承认,当年参与暴动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受他们影响“培养”出来的那批人。
儿童教育事关百年大计,好的童书不仅传授知识和审美,塑造生命和灵魂,也是启蒙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劣质图书带来的精神污染,和将会造成的潜在后果,无法估量,有可能会毁了孩子一生。
5月28日,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进行回应,将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教材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但这种只停留在表面的道歉和整改,显然平息不了国民众怒。5月30日,教育部发布最新消息,已成立调查组进行全面彻查,对存在违纪违规问题的责任人将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已故国学大师曾仕强先生曾经说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文化之战,而且已经悄悄开始了,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
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腐蚀和渗透,最为隐蔽和歹毒。只有将相关著书、编书、出书和荐书等流程纳入常规监管和整治范围,并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发动群众力量,才能让劣质图书无所遁形。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好河山重在根基。事关下一代的教育、祖国的未来,“小事”不小,也绝不能小。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参考资料:
1. via光明网《童书出版,别只有铜臭味而无责任心》
2. 道客巴巴《新中国成立70年来童书出版主题、形态与传播方式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