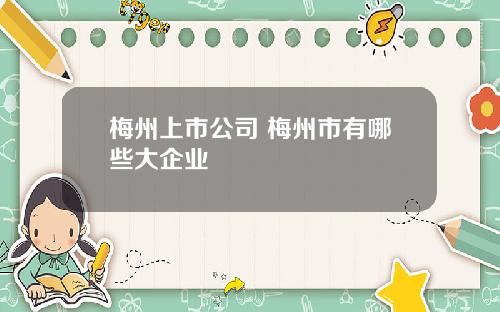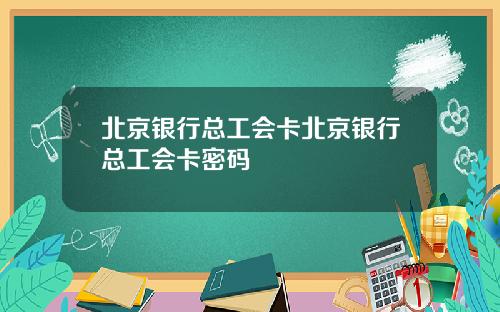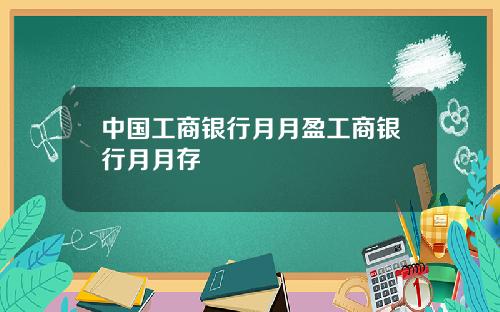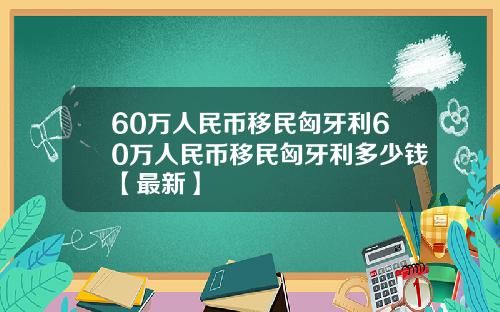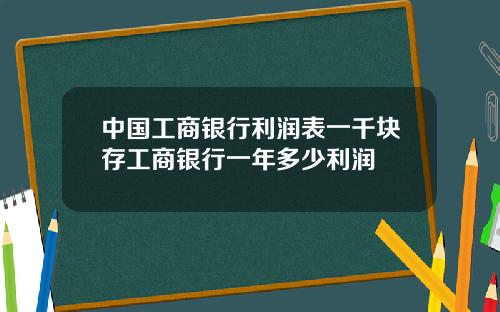<?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11 中国人治理智慧的本质
1 中国人道法自然的管理学
20世纪9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就预言中国人一定会有治理智慧与世界分享。但是苦等了二十几年后,我们却没看到中国管理学者们系统地提出一套本土管理学体系。雷军说互联网思维中有一项“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费舍尔教授也说,中国确实已经在管理方面为世界做出了贡献——有关如何组织与引领“更快节奏的运营”。西方管理理论近来最强调的弹性、易变及快速反应,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企业家身上已经有了很好的体现,只是现在很少有学者能静下心来好好研究它们,以总结中国的本土管理理论。
总结以上各章所述,中国管理哲学首先重视的是关系管理,这包括五个动态平衡之道。
其一,关系管理的目的是与一群人建立信任关系,一个人需要维持关系中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的动态平衡,在特殊的人情交换与普同的均分法则间寻求平衡。同时,要在使用权力和经营信任间保持平衡,使得很多长期的、短期的工具性目的得以实现,而人际信任又能不断增强。
其二,一个人经营这些关系,其动机的一方面是加入领导圈子,以集体力量获取资源,得到更多人情交换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圈子,这是完成个人长远目标的本钱。但好的圈子经营也要维持圈子边界的开与阖的动态平衡,只有动态平衡做好了,才能保持圈子可大可小。这正是平衡脱耦与耦合的道理。
其三,动态平衡圈子内的特殊照顾与圈子外的公平分配,做得好才能兼顾圈内的紧密合作及圈内与圈外的和谐,如此,一个人才能做到弹性地动员或不动员、多动员或少动员他的人脉资源。中国人的弹性大、变化快、适应力强概源于此。
一个人经营圈子的目的在于“裂土封侯”,也就是可以自组织出独立或半独立的团队或组织。对组织管理而言,系统就是组织;对公共管理而言,系统就是社会,其领导者也要懂得“放”的哲学,给人自组织的机会,系统才能多元并存,保持弹性,拥有较强适应力,生生不息。
其四,“收”与“放”之间也要保持动态平衡,也就是平衡收权与放权。要考虑不同的情境,决定是多用自组织治理的原则而少用层级治理机制,还是多用层级而少用自组织。同时又要观察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是否失衡了。一方独大,过犹不及,对系统都会造成伤害。
其五,“放而不乱”还需要维持非正式规范的“礼”及正式制度规章的“法”的动态平衡,法礼并治,相辅相成。“法”能保住行为的底线与公平的准则,“放”就会有较多的自由空间,“礼”则使得自组织不会滥用自由空间,中国传统智慧强调的“恩威德并济”正是这个道理。
那我们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与从西方发展出来的管理哲学有何不同呢?这是一个很大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很难回答得完整周延,但我还是要试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中西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并不是“是”或“非”的问题,也不是“有”或“无”的问题。关于我们的组织现象,西方管理理论都有谈到;关于西方管理理论,我们也多有实践。不同之处在于程度,也就是“多”或“少”的问题,以及出发点的不同。
中西方管理的区别并不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也不在于科学管理和人本管理的区别。西方也有集体主义,只是西方的认同更多地建立在种族、阶级、性别、职业、年龄等因素之上。当然,相对而言,西方更强调个人主义。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则更多地表现为在圈子中的行为,所以很多学者称之为“关系主义”。
西方也有人治和礼治现象,他们也很重视文化、愿景等,并设计了制度鼓励自组织,如晚近发展出来的内部创业制度与自我导向团队。但西方更重视的是流程、规章、制度,管理思维以规划与控制为主,因为这套管理预设了系统中的人是“理性经济人”,所以组织是可以被理性设计并被理性控制的,这就是层级系统的思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从马克斯·韦伯的层级制与泰勒的科学管理运动开始的,这是一个以组织管理名家史考特所说的理性管理系统为主轴
[1]
,但不断以自然管理系统加以修正的思维,如巴纳德的“经理人的职能”、梅奥的“霍桑实验”
[2]
和人群关系管理运动、塞尔茨尼克的新制度主义
[3]
及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学派。
而中国的管理法则刚好相反。我们总以“道法自然”的思想来看待管理法则,所以自然管理系统是主轴。与之对应,自然系统尊重人的社会性和情感性和对环境的顺应性,强调“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构,所以我们在治理上主要采用网络和自组织,依靠成员间自发的合作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因此,中国人天然就更熟悉自组织治理机制,辅之以层级治理。
当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无法仅靠单一治理方式保持系统的秩序与稳定,我们都是在各自的基础上,吸收另一系统的特性。良好的管理常常是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糅合在一起,是层级、网络、市场三种治理机制的结合,并互为补充。
西方的管理以理性系统为主,辅以自然系统的特征。因此,西方的组织通常更强调“对事不对人”,以流程、规章、制度为出发点,重视对事进行规划、执行、考核和奖惩。通过设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和流程,使员工成为大流程中的“小螺丝钉”。只是管理者们后来发现这些“小螺丝钉”开始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开始怠工和不服从管理,进而才产生了员工关怀、愿景管理等一系列人本管理的元素,以提高“小螺丝钉”的工作满意度、归属感和成就感,最终增强工作动机。
与理性系统相对应的是自然系统。它相信社会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是需要关系、小团体、归属感与信任感的,所以人的结合是自然生发的,很多组织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靠理性去设计与控制的。中国的管理在一开始就是从人出发,以自然系统为主、层级系统为辅。因而,中国人重视先管人再管事,强调“人对了,事就对了”。这样的管理哲学重视看人、收心、培训、因材器使,然后授权赋能,以期“我无为而事自成”。中国的领导者不会详细规定每个工作细节,而是在前期做好关系管理,建立信任之后,事情就是你的,所以领导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所以,中国的管理哲学是先承认自组织,效率不是来自规章制度、规划控制,而是来自自组织。这是整个中西方管理思维中最不一样的地方。
但我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自古还是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层级制度呢?而且中国在19世纪以前一直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层级组织。中国组织中层级系统的成分,是为了在管人的过程中,更好地规范行为底线,增加合作性并增强人际信任,也就是说,以法辅礼,以层级治理辅自组织。我们也都知道,这些自组织固然非常有活力,但活力到了最后往往就乱了套。乱了套的结果就是互相掐,互相卡,互相争斗,甚至最后变成“藩镇割据”,更糟糕的情况是变成“军阀混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为了维持自组织单位之间的稳定,就必须有层级制度的治理机制来加以控制。但在这个层级控制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非常强调礼治秩序和价值、文化的引导,并且礼治秩序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和西方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的管理哲学虽然强调自组织,但也仍然需要保持层级权力和自组织之间的平衡。如何平衡?在我国政治组织的实践中,知识分子扮演了上下之间“桥”的角色,重视“皇权”和“绅权”的平衡,皇权代表的是由上而下的层级控制,绅权代表的则是由下而上的自组织。何时放权给乡绅,何时收权于中央,正是收放自如的动态平衡之道。
我们总看到中国人围绕在关系管理、圈子经营、自组织治理、系统布局、动态平衡中发展出来的一套管理艺术的一个方面,但在实务上,我们有时会滥用、错用关系和圈子,导致过犹不及,阴阳失衡。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必须看到它“阳”的一面——基于合作、弹性而有的快速反应及自组织小细胞直接接触外在环境而产生的自适应,这使得我们有了“更快节奏的运营”、更多的边缘创新、更基业长青的系统。这“阳”的一面符合未来信息社会最需要的一些管理思维,把这些智慧化为真正的管理实务,并以科学方法研究出来,是我们这一代政府及社会领袖、企业家、社会科学家、管理学家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责无旁贷。
2 中国人的管理基因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治理智慧呢?这与我国社会的特质有关。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展现了与西方社会十分不同的特质。下面我整理了社会学家如费孝通,本土心理学者如杨国枢、黄光国等人的研究,归纳出如下几项。相对于西方的团体格局或社会类属格局,我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格局是差序格局;相对于西方人的普遍主义道德观,中国人的道德观是特殊主义的;相对于西方的法治秩序的社会,我们维持社会秩序主要靠礼治。在礼治传统之下,中国社会的权力不来自制度,也不来自个人魅力,而来自“知书达礼”的教化权力。另外,我们中国人的主要组织是以家为中心,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而成为圈子形态的小团体,这不同于西方主要的俱乐部式小团体。这种自组织的“家”自古成为地方的宗族,宗族的发展使得我们中国人有着很强的自我组织能力。
下面,让我们先看看这些社会的特质对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有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中国人遵行关系主义或特殊主义的行为法则,人情交换与经济交换混而合一,所以长期伙伴关系与其关系管理总是中国人治理智慧的核心,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网络式经济与网络式组织。
第二,差序格局的结构,亲亲有等级,使得中国人会从内到外分出关系远近,不同关系适合不同的互动法则。在组织之外,关系是获取资源最重要的依据,不同关系适合不同资源的取得,有的需要亲如家人,有的则只需弱连带,而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就需要建构一张由强到弱、层层包括的人脉网络。在组织内,差序格局使得中国式领导由内而外形成了一个亲信班底及圈内人的领导团队,以领导为核心,因关系远近而层层向外,各自担任不同的领导职能。
第三,以“拟似家族”为中心的组织方式,不但使中国的组织保持了家族组织的特性,而且使中国式领导保持了家父领导的风格。在组织之外,组织领导也喜欢与长期的或有潜力的生意伙伴拉近关系,如同拜把兄弟一般,形成中国人关系类型中十分特别的一种类型。
第四,中国人在宗族自治的训练中,十分擅长自组织。从海外的中国人处处能够经商,自组织成为企业,创业特别发达,甚至成为一些地区的经济主导力量,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组织传统。中国人在组织上表现出旺盛的创业精神,“宁为鸡首,不为牛后”,所以中国网络式经济的活力最主要来自创业。在组织内,中国式领导也要懂得运用中国人的自组织能力,建立利润中心制度或内部创业制度,以鼓励员工创立自组织,自行解决问题。
第五,中国人的治理智慧中强调以教化为主的权力,这使得中国式领导首重德行,也就是以身作则,上下一致守规范。次重说理,不能以审判、奖惩为乐事,更要“给个说法”,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在我国,赤裸裸的惩处是不顾念人情的,做事不留余地的结果是“是非之理”不见了,只剩面子之争,人们可以因此持续数年斗个你死我活。
第六,关系运作的原则要靠礼治,教化说理的背后也是礼治,所以我们中国人重视礼治秩序。应用在我们的治理智慧中,展现的是组织文化的重要性。文化建设是我们中国人治理智慧的首要之务,而且它不能只是反映组织的愿景与特色,同时要包容中国人为人处事的一套规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国人共同遵守的规范。
但是,我国的礼治传统是建立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之上的,不变的社会,不流动的一群人,这是传统和经验有价值的原因。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天天在变化,组织也是这样,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是不是中国传统的治理机制就此不再有效了呢?
我们固然在变,但我们又不可能将我们的基因一夜之间彻底改变,所以我国传统社会的这些特质依然清晰地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反映在我们的经济行为之上,我们依旧是十分强调关系导向的,依旧喜欢“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地去创业,依然有差序格局的思维。这些特质仍有其不变之处,管理研究必须面对它们,找出适合中国人的管理方式,不能只是斥其为糟粕或对其视而不见,一味地希望引入西方的管理理念,一夜之间改变中国人的基因。
除此之外,中国人这种强调创业、网络式组织、礼治与文化建设、自组织的能力,又暗合了信息时代服务业经济兴起后,西方管理学界开始重视的迈尔斯等人提出的“人力投资”管理理论。
[4]
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并不全然是过时的,在新时代,它可以找到它的新义,以符合复杂系统所需要的治理思维,这更是我们的管理研究需要正视的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人开始重新发掘中国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国学热一时传遍大江南北,国学入管理也成为一时的潮流,我看到此现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中国人的治理理念,比如“御将之道”“做生意之前先做人”“修身”“诚意”“修养”“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恩德”“知所畏惧”“人脉”“熟人”“报”“同”“人情账”“事师”“齐家”“班底”“礼治”“教化”“德行领导”“差序格局”“礼法并治”“法尚俭约”等,其实都是围绕在关系、圈子、自组织、复杂系统与动态平衡周边展开的。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如何能研究中国人的治理智慧?
西方人的管理理论谈中国管理,说到今天,总是在说“关系”,谈到关系的内涵、关系的运作、关系的功能、关系的分类、关系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却无法深入研究中国人关系结成网络后的结构特色,对形成圈子的特性研究甚少,对基于关系、圈子的治理机制的研究更付之阙如,有赖我们的本土研究补足西方学者对我国的误解或了解不足。
然而,一味地强调本土特色又不免会落入“关起门来当皇帝”的陷阱中,最后变成国学式的探讨,甚至成了哲学,更有甚者成了玄学,而无法融合西方学术实证与实用的方法,自然得不出有现代管理学意义的理论。
所以我的忧虑之一是我们不能把国学当管理学的书来学。本书一直以《中庸》当作中国人治理智慧的根本,希望《中庸》里的为人处世的道理能以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结构分析法及复杂系统加以研究,借之拓展本土的管理科学研究。但直接把儒家经典当管理书读,则失之过分了。毕竟,这些经典是教人为人处世之道的,一个懂得如何为人处世的人可以做好管理,也可以做好很多其他事情,所以它对管理的帮助是间接的。直接把经典当管理书来读,想在书里一字一句地分析出管理内涵,会有误导或强做解释的危险。比如,儒家传统是重士轻商的,学了这个概念,总在自称儒商,甚至以自己是知识分子为荣而不以管理专业为职志的人,那是文化人、教授,不是企业家和经理人,他如何做好管理?所以强调学理和文化甚于管理,或非要做个“儒商”不可,都会矫枉过正。
尤有甚者,把儒家经典当管理之书,强在其中解读出统治之术,那就更可怕了。那既污辱了国学,把国学变成了心灵鸡汤、职场励志或追求效率、效果的书,也污辱了管理科学,把科学所需要的方法与严谨完全丢弃了。《论语》要教的是领导者如何诚意正心修身,是要领导者懂得自我节制,而不是要教领导者统御之道或战略之学,把《论语》当管理书会有误读孔子意思的危险,不得不慎。
忧虑之二是我们太看重传统智慧谈谋略的部分。《孙子兵法》一直被视为中国管理宝典,好像管理就是战略。等而下之的,更把权谋之术当成了我们中国人管理哲学的中心,把法家统御之术或厚黑学当成了我们中国人治理智慧的核心。我们讲求阴阳平衡,但我想强调在关系管理及圈子经营上要以正为主,以奇为辅。以奇为主,甚至只见其奇而不见其正,都是善治的大忌。中国有五千年文化的精华,其实也有五千年文化的糟粕,善于权谋、工于心计、密室政治及结党群斗一直是中国人善治之道的最大敌人,一个不慎,国学入管理得到的就是糟粕而不是精华。
忧虑之三是“国学”一旦套上了“国”字,某些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之挑动,国学就成了管理的《圣经》,像是意识形态般地让人顶礼膜拜,不可挑战。一方面,这正是管理的大忌。经理人不学管理理论,只相信自己的“管理技术”,必然会失之偏颇,今天的成功经验就会变成明日的不知变通,埋下失败的种子。但顶礼膜拜某一管理理论则更危险。尽信书不如无书,其实,管理就是一个持“经”达“变”的过程,在理论中寻找启发即可,运用时则要知变通,否则,照着理论去治理一个系统,大概也难逃失败的命运。所以国学不是管理理论,更不该让它成为使我们顶礼膜拜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的情绪下,我们会产生“四大发明”的荒谬,拿着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就说“西方有的,我们都有”,再也不肯向西方学习其现代管理学中发展出来的哲学、理论与技术了。
忧虑之四是国学入管理容易流于哲学式的讨论,它谈的是中国人的管理哲学,这会变成对应然的探讨,而不是对实然的研究。所以不要总在国学中找灵感,把《易经》《论语》《老子》《孙子兵法》等都看成管理学的书,就很难让我们将对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探讨与现代管理学的实证方法结合,所以既无法证实(或证伪)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意义,由此更难形成一套属于中国人,也适用于中国人的管理理论与管理技术。
本书谈到了从《中庸》中的哲学性的启发得到的要义,但关系管理、自组织治理及复杂系统的动态平衡,都不该止步于哲学性探讨。事实上,关于这些智慧,我们早已有了相当多的科学研究。四五十年来,关系研究在本土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中早已有了比较成熟且极其丰富的成果。自组织源自治理理论,而做治理理论相关研究、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者亦有四届五人之多,其中奥斯特罗姆更是直接以自治理理论得奖,其他社会学大师如格兰诺维特及鲍威尔也对这一理论着墨颇多。复杂系统理论更在圣塔菲研究所的倡导下成为一门跨学科研究的崭新领域。虽然关于自组织与复杂系统的研究还处在较初级的阶段,很多研究方法还有待探讨,但扎扎实实的科学性实证研究已经存在,国学一定能给这些研究提供重大启发,但它却不能总停留在哲学思辨的阶段。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终于开始自省,这让我们看到了本土管理学的一片桃花源。
过去,一群受过国外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总把西方整套管理学,包括理论与方法,一起搬到我们这片土壤上。工作满足、组织承诺、公民行为、组织正义、工作特性、组织结构、社经背景(不同的社会类属如性别、年龄、宗教)、社会人口学(一个组织中不同社经背景的员工组成的方式)及个人人格特质(如内向、外向、内控人格、外控人格等)成了解释员工行为的主要因素,由此发展出如何激励员工和如何组织员工工作的管理理论。这些因素在中国组织中当然仍有其解释力,仍然值得我们据此研究中国组织的管理问题,但是,这些概念主要是围绕“个人”的问题,不足以说明中国人的主要管理行为都围绕在人与人的“关系”“圈子”上。要真正了解我们中国人的管理行为,仍需要摸索出很多贴近于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概念,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有其价值,却不足以一窥中国管理之全貌。
3 道重于术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国家领导人一直管理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也管理过到19世纪为止人类史上最大的组织。管人也罢,管组织也好,中国人都有过傲人的经验。当然,我们不必拿着老祖宗的治理智慧拒绝西方现代的管理学。然而,今天我们的管理学界又好像有点儿妄自菲薄,西方提出什么,我们就跟着谈什么,从不问一问从西方传来的这些管理思潮与管理技术到底适不适合我们使用。所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正是使管理思想为我们所用的第一步。而了解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管理人类历史2 200余年(以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开始算起)中这个总保持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及最庞大的组织,更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让本土化、适于我们所用的管理真正扎根于中国。
那么我们的老祖宗有些什么样的治理智慧呢?我在这里总结了我的一些观察。
第一个就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我们所知,《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里面谈的都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它奠定了中国人两千年来的道德基础。它不是一本谈战略的书,更不是一本谈管理的书,但它却被我们的祖先视为“治天下”的宝典。现代中国人一谈老祖宗的治理智慧就喜欢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谈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是战略管理思想的精髓,在现代管理学上有其意义。但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讲“半部《孙子兵法》治天下”,可见我们谈管理的重点不在战略,而在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学会做人的道理,是中国人治理智慧的起点,舍弃了这一点,奢谈中国人的治理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再直接联想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做生意之前先做人”。做生意就是完成交易,经济交易与社会交换的治理正是治理理论的起点。中国人善于将价值链分解,由不同的组织负责,再用交易的手段整合分解的价值链,就现代管理学的术语而言,这就是网络式组织的结构。所以商人管理组织外的“相与”网络是比管理内部作业流程还重要的活动。而要做好这份管理工作,做人是首要之务。所以,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营造双赢的机会,建立持久的关系,是中国人从商时必修的功课。
相对于“做生意之前先做人”是“律己”,中国人也强调“做生意之前先看人”,要有智慧。“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说明的就是皇帝在找到好臣子之前,要先看臣子的品格,不孝之人是一定不能录用的。同样地,商人找“相与”或员工的时候,“观其眸子知其心意”,也就是看一个人的眼神来判定其人品,獐头鼠目、油嘴滑舌之辈是一定不能成为伙伴的。“做生意之前先做人”“做生意之前先看人”,说明了中国人谈管理的重点在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以及如何找到值得信任的人。
谈到做人,谈到信任,马上就让人想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也就是说,中国人从管理一个组织到管理天下,都从修身开始。换言之,管理别人之前,先要管好自己。在中国,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是不配谈管理的。所以管理绝对不只是定好制度、规章、流程、工作设计、奖惩与激励,更重要的是领导者的领导。而做好领导也不只是懂得“领导术”而已,“道”更为重要。中国人相信,好的管理不只是知识、技术、制度、流程这些“硬实力”,文化、愿景、领导力、信任这些“软实力”更重要,而软实力的根本始于领导者的修身。
“修身”之后还要“齐家”,这是指要把周遭的一群人管好,包括亲信、班底这些圈内人。不只是管好领导者与“家人”间的关系,还要管好“家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一群人相互信任,精诚团结,乐于合作,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整体战斗力。最后“家和万事兴”,才能够成事,而且成大事。西方的信任理论指出,人不可能经营信任,只能够经营可信赖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术”、用“谋”使别人信任我们,只能自己表现出可信赖行为以争取别人的信任。“齐家”既要自己表现出可信赖行为,还要使“家人”都表现出可信赖行为,这才能使大家相互信任,易于合作。《论语》之所以是中国人在管理上的宝典,正是因为它陈述了“修身”与“齐家”的基本道理。
企业家不但要成事,还要谋利,所以中国人延伸了“修身、齐家”的道理,提出了“以义制利”的观念。义者宜也,也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中国人谈交易,讲求的是诚信无欺、顾念人情与公平合理,如此“合宜”的行为才是得利的基础。至于其他“技术”层面的东西,用孔子的话说是“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孔子的这段话意在说明,离开了大道,即使可以成功于一时,也无法持久,换成现代管理学上的说法就是无法成就基业长青的组织。符合了义理,也能谋利,而且谋得的是百年之利,是基业长青的大利。以“术”谋利,谋的则只是小利,更是短期之利。或许中国人重道轻术的管理思维阻碍了我们发展现代管理技术,但看看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谈的“第五类领导人”,是不是有些像强调修身齐家的中国传统中的好领导?这似乎是中西一致的建立基业长青、百年组织的思维。
最后,中国人强调垂衣拱手而天下治,也就是无为而治。现代组织要做事,还要成就很多事,不比古代乡土中国,只要保境安民即可,所以这是十分不符合现代意义的管理思维。但是,这种思维却意在说明“相无才,天下之才皆其才,相无智,天下之智皆其智”,一个领导人作为太多,反而会阻断员工发挥的机会。换成现代管理学的术语,就是领导要授权赋能以鼓励员工自己形成组织,主动解决问题,提出改善方案。所以相信员工的动机,相信员工的能力,鼓励员工的自我组织,正是“我无为而天下治”的基本道理。
这些信手拈来的中国传统的治理智慧说明,中国人的管理思维是“道”重于“术”,做人先于管理,安人先于成事。简单地说,就是人比事更重要。这其实有其现代管理学上的内涵,即治理比管理(这里的管理指的是日常管理,是狭义的、层级制意义下的管理。今日,治理仍被放在管理学中谈,所以广义的管理包括了治理)更重要。换言之,市场、层级、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的动态平衡才是善治之道,单单的层级治理是远远不够的。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即在于,从复杂系统、自组织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人传统的治理智慧。这些治理智慧绝非过时无用之物。一方面,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其千年来不变之处,虽然在西方潮流的影响下,我们在不断改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仍然是一个家族观念扩大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仍然是一个顾念人情、希冀和谐而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所不变,所以这些传统智慧对管理拥有千年儒家传统的中国人而言,仍有其价值。另一方面,这些治理智慧可以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持,尤其是社会资本、社会网、复杂系统理论的支持。在信息经济、服务业经济的时代里,它对新时代的管理问题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我们固然不必高唱西方管理无用论,但也不必妄自菲薄地“全盘西化”,否定这些传统智慧的价值。
4 中国经典管理理论
新管理研究典范——复杂系统
我要说明的重要的一点是,复杂系统研究的观点吻合了信息时代被网络化的社会的需求,自组织过程、网络动态学、复杂自适应性、非线性的系统发展等成一时显学,并与物理、生物、生态、脑神经医学等各学科的复杂理论的概念不谋而合。这一类研究已经萌芽于20世纪,并在圣塔菲研究所中“汇流”,推进了浩浩荡荡的复杂科学的发展。
复杂理论发现,物理世界中的自由分子会有自组织现象,最后因结构化而形成一些固定的“秩序”。同样的自组织与结构化现象也出现在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之中。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低度社会化”观点就像水蒸气状态,每一个人都是自由分子,在空间中随机运动,遇上任何人都可以产生互动。“过度社会化”观点又像固态的冰,所有动能都不见了,没有能动性的个人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在场力形成的铁栏内处处受制。
[5]
而我们实际的社会却是在这些不同的状态中不断地转变,更多的情况是大家既受场力的束缚,也有能动性,更可以集合,也就是自组织出一些固定的结构,进而改变这些场力。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领域,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一个产业或一个组织,可以被我们称为“场”,场之内有许多作用力,我们称之为“场力”。组织社会学者狄马吉与鲍威尔针对组织中定义的“场”为:“组织场是一群组织组成的社群,它们从事类似的活动,并屈从于相似的声誉暨规则压力之下。”
[6]
换言之,使组织“屈从”的场力包括信息类的,如声誉、口碑、顺应流行等,以及规范类的,如服从风俗、道德、法律与制度等,也就是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法与礼。
从社会网的观点来看,场力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行动者身上就决定了行动决策,而是通过一个行动者身旁的关系及社会网来作用。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接受了某一信息,这会使此人也相信此信息;一个人周围的人大多服从着某一规范,就使得此规范具有强制力,使此人也遵守。场力如何作用于个体关系的形成,以及个体如何在社会网结构中取得结构位置,是社会网研究的第一个议题。
进一步来看,个体关系与个体结构位置(配合着场力的作用)会影响行动者的行动决策。一群人持之以恒且相互合作的行动则会改变集体的社会网结构,从而使相同的个体行动在不同的结构中“加总”出不同的集体行动,而这些集体行动一旦持续甚久又被制度化了,则会形成新的场力。而社会网研究正是要辅助解析这个从集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其中,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结构是这个过程中间的“桥”。而从个体到集体的过程中,集体的行动结果绝对不是个体行动的简单加总而已,它是个体行动与网络结构共同演化的结果。一路从个人到小团体或圈子,再到各层子系统,如平台、社区、城市等,再到最大的系统,如国家、经济体、社会等,会层层涌现出独特的集体特质,尤其是各层系统都会涌现出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这正是复杂思维对化约主义理论提出的最核心的修正,一加一不完全等于二,个体的加总之外还会涌现出一些集体的特质。
对这些新的个体行动与网络结构共同演化的研究,正启发着社会科学与管理学发展出自组织、自治理、复杂系统、复杂网、网络动态学、系统常态和非常态的演化,以及自适应与非线性系统发展的理论,渐渐地会产生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的新研究典范。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化的社会,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中,我们发展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概念,这会启发很多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研究获得新方向。其中有一些在今天的研究中已初见成果,有一些还有待更多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还有一些是今日的科学研究工具没发展出来的,这些也会是国内、国际社会科学与管理学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议题。
对本土管理学的启发
我认为,中国人的治理智慧可以启发复杂系统管理学的研究,荦荦大端如下所述。
(1)关系与网络化研究。
第一,系统网络化。以组织为例,外部网络化、分包体系、挂靠、承包、商帮、地方产业网,和很多今天西方已有的研究,如战略联盟、授权经营等有何同?有何异?它们互相依赖,共同组成一条价值链。
第二,内部网络化。这就是“跑马圈地”“诸侯经济”的分权制度,中国人只要一采取这种制度,往往可以调动员工极高的积极性。在中国如何做才能让部门有独立生命?它与西方已有的任务导向团队、成本中心制度、内部创业制度等,有何同?有何异?
第三,差序格局的集体领导。第一层是亲信班底,第二层是圈内人,第三层才是一般干部,是以领导为核心依关系远近层层外推的管理团队,领导靠着亲信、班底与圈内、圈外干部才能管理员工。西方有个领导—部属交换理论与此最接近,但明显地,中国的实务复杂得多,有待我们研究。
第四,修身才能治理。修身是为了吸引相同气质的人协力同工,是建立个人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引导组织愿景与组织文化的过程。西方管理理论到晚近才谈个人与团体的修炼(代表作为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7]
),中国发展得成熟很多,这对管理理论有何启发?
(2)圈子研究。
第一,齐家。齐家就是安人。如何建立圈子、经营圈子,如何使得团队成员和谐相处,先安人才能做事。而圈子理论得到的研究还很少。
第二,家长式领导。恩、威、德并济,以营造领导组织如严父又如慈母般的带领,要教化、关怀员工,使员工有归属感。樊景立与郑伯熏提出的“家长式领导”是不多的被国际也认可的本土管理理论,值得深入研究
[8]
。
第三,包容与弹性。和谐要和而不同,包容不同,为人的协作预留更多的弹性空间,以随机应变,保持工作弹性。弹性、易变正是中国组织的一项优势。中国式的弹性专精制体制该如何建构?如何运作?与西方有何不同?这些是值得深思的研究。
第四,差序格局下的礼。中国是礼治社会,礼是外部网络中关系运作的原则,也是内部网络中人际协作的不成文规则。人际相处要靠这套为人处世的规范才能和谐协作,它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在差序格局思维下,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法则,如何保证公平?如何运作顺畅?
(3)自组织研究。
第一,礼法并治。完成系统目标要靠流程、规章、组织结构与正式制度等“硬实力”,但系统基业长青要靠人际协作、互信、合作、共同愿景、共同文化、非正式制度等“软实力”。“软实力”的背后有一套人际协作法则,在中国就是所谓的“礼”,所以礼与法缺一不可。西方总以法为主、以礼为辅,中国人总以礼为主、以法为辅,这是有趣的比较研究。
第二,信任与分权。信任既来自制度,也有“你办事、我放心”式的关系型信任,所以治理组织不但要建立制度创造信任,也要找到值得信任的人,在互动过程中建立信任关系,这些已有充分的研究。但是,如何使信任关系成为圈子?圈子如何发展成自组织?自组织过程是什么?这个领域仍有很多研究的空间。
第三,法尚简约。系统要想做事,就不能没有流程、工作标准及正式法规,但是要给系统留出弹性空间,因为苛法与严法会扼杀创意、弹性及员工的工作动机。礼崩乐坏之后,末世王朝往往法条越严,法网越密,结果是有些人最会钻法律漏洞,反而让君子动辄得咎,小人无往不利。如何在自组织中建立自治理机制?自治理机制如何能够运作?这在奥斯特罗姆的研究中多有呈现,而中国本土的特色呢?
第四,崇道与教化。教化为主、控管为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特色。高举一些做人原则以建立愿景及行为底线,让良好的文化规范来制约人的作为,重视有弹性、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如果少了人心的约制,这种空间就容易变成“一放就乱”的温床。所以要重视系统成员的教育,尤其要重视愿景与文化的人心教化功能。好的愿景与文化体现的是礼和治理机制的整合运用,而非奴化教育。
(4)复杂系统研究。
第一,中庸之道。其核心内涵之一就是动态平衡之道。西方管理理论正在发展管理对立双元体的想法,中国却已有了很多实践,在放权与收权间,在法与礼之间,在层级、市场与自组织三种治理机制间如何取得动态平衡?在组织设计里,以人为本或以事为主也需要执两用中,过犹不及,过分重视“硬实力”不好,但过分强调人际关系也会出乱子。
第二,取势。“势”是中国人重视的很有趣又很有价值的概念,是对复杂系统演化方向的一种观察。如何审势,从而趁势而起、顺势而为?如何把握节与度,从而掌握“拐点”,因势利导、审时定势?随着大数据的使用,过去这类“势”的涌现与“势”的“拐点”的问题变得可以被研究,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去找到一个系统的“拐点”,大概是未来最有趣的理论发展了。
第三,布局。布局因观势而有,如何审势乘时?如何倚势待机?如何应势而作?在可预见的重要节点上布好人脉,好的起手式才会带来一路顺畅的棋局,这些是中国人独特的韬略思维,它和现在的战略理论如何相辅相成?这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四两拨千斤。中国人的太极拳的思维是顺势而不逆势,掌握轻轻的力道就能促使系统发生改变。调控的时机不对,力量不对,过犹不及,都无法有效让系统存续。所以掌握“节”十分重要,而大数据与复杂系统的研究正好能告诉我们这些“拐点”会在哪里。
第五,生生不息。我们中国管理学的最终理念在讲一个生生不息的道理,这也是日本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之后,感受到的最主要的哲学观,并用之经营他的索尼公司。
细究起来,这些其实主要都是治理之道,而非日常管理。所以传统中国谈的多是“善治”之道,而不是工作分派与控制之道。修身、齐家之后可以“治”国,而不是管理国家。只是治理理论如今仍被放在管理学中谈,所以本书不再加以区别,而一概称这些为复杂系统管理学。
我认为,中国人的治理智慧能为复杂系统管理学开辟出一大片桃花源。
[1] Richard Scott. Organizations: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 NJ: Prentice Hall,1998.
[2] George Elton Mayo.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3] Philip Selznick.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8(8) :47—54.
[4] Miles Raymond, Douglas Creed.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Managerial Philosophi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5(17) : 333—372.
[5] M.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 : 481—510.
[6] Paul J. DiMaggio, Walter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Conformity and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New Heaven: Yale U. Press, 1982.
[7] P. M. Senge. The Fifth Discipline: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London:Random House,1990.
[8] 樊景立,郑伯埙.华人组织的家长式领导: 一项文化观点的分析[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0(13) :12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