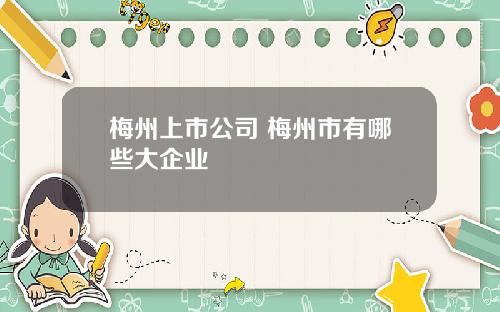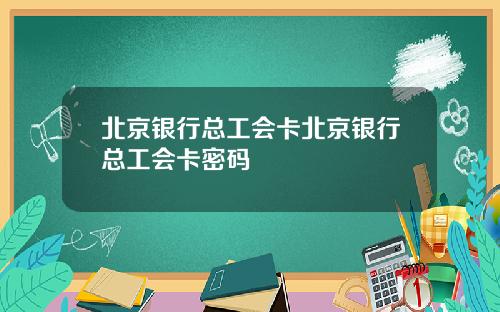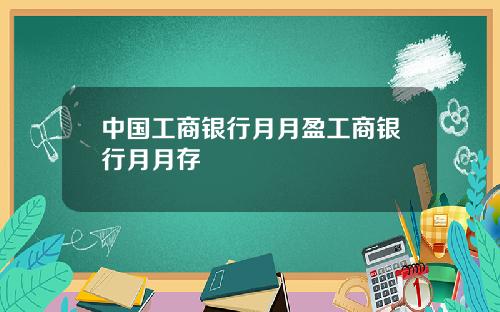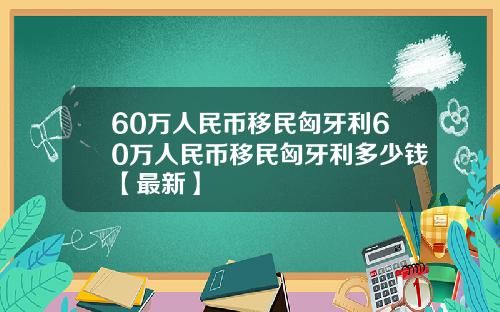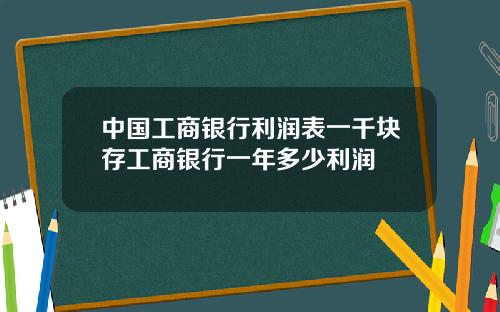机构投资者评论Institutional Investor Review:记录最杰出的投资人物与事件
出品 | 机构投资者评论 IIR
请尊重原创,抵制洗稿,违者必究
转载授权、商务合作等请联系后台
《巨人转》中有句经典语录,“时间可以使一切事物成熟,时间一久,一切都越来越清楚,时间不愧是真实之父”。
30年前,叶庆从北大毕业;如今,IIR又在北大附近见到了她。这不是我们的初次相识,但又是一次全新的对话。
十几年前,叶庆和她的校友重新聚首,带着熠美
(YiMei Capital)
落地国内
(建立熠美投资亚洲业务)
。那时,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刚刚实施
(2007年)
,创业板还未正式推出
(2009年推出)
,美元基金出身的叶庆还喜欢招募“Specialist”
(专才)
。
十多年来,叶庆一直呼吁人民币基金市场出资人结构的多元化,其中就包括众人期盼的险资、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等长期资本,因为那曾是叶庆在海外做投资时LP结构的“理想国”。
IIR以往将熠美定义为:国内第一批探索受托管理人民币引导基金的专业机构之一
(2010年)
,
而这一次我们见到奔波在北大的叶庆时,她又开创性地成为北大教育基金会
(全称: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德赛母基金”的专业受托管理者。
在我们看来,这无论对国内高校教育基金市场还是股权投资行业,都是标志性的突破
(见IIR此前报告:
重磅年报:主流机构LP100 配置全年报 · 2021年 | IIR
)
。
做先锋,就是在还未有路时,向他山之石求证,在漆黑中摸索,持续不断做市场教育工作。
熠美在国内人民币引导基金市场开创性地做了双币种母基金管理的探索,12年后的今天,在熠美的账本上,引导基金的三倍回报,IRR 22%以上,叶庆也能从容地带着这份成绩单,为她长期“帮忙”、从未有所期待的母校基金会,探索更符合学校长远发展目标的资产配置模型。
时间,“洗”出了专业机构投资者,也“洗”出了叶庆作为一个商业世界“高知”女性管理者的“Street Smart”——因地制宜、择“善”固执,看得准,吃得透,守得住。
捐滴成河非朝夕之功,国内高校教育基金还在“婴儿期”
IIR创始人Emma:IIR此前与成思危基金、中风投联合发起一个高校教育基金的专项课题,过去两年,我们与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有一些调研交流和粗浅观察。我们很早关注到,北大教育基金会前年开启了一个公开遴选,去年熠美拿到了这笔大额委外投资。于我们的视角,这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我们也了解,熠美很早就有管理海外大学endowment的经验,从您的视角,国内的高校教育基金市场目前在什么阶段,海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配置模式,于我们有借鉴意义吗?
叶庆:
中国人的传统是特别重“教”的,虽然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国情体制都不相同,但有些共性我想是存在的。
如果要对标海外一流大学,不管耶鲁、哥大
(哥伦比亚大学)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大学)
,还是欧洲的牛津,现在他们的endowment规模都是Billion Dollar俱乐部,去年业绩也非常好,但这绝非朝夕之功。
牛津有900多年历史,UPenn也有将近300年,这些最佳实践的背后,首先都是evergreen的长期思路。而这背后最大的动因是,只有当endowment的盘子足够大,通过科学的资产配置,每年的现金流才能回来,支持学校的经费支出和长久发展。
到今天,我们也能看到,
这些一流大学的校友捐赠基金,都不是靠谁偶尔写个10个亿支票做大的,他们更多靠的是小额高频,捐滴成河的积累,超过一大半是校友大范围的“小钱”捐出来的。
而这类“长钱”从配置上看,一级市场、PE类资产作为high growth driver
(驱动高增长)
的品类,可以很有α。如果有一个“对”的资产配置模型,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学捐赠基金里,它都几乎是一个真正“拉”(高)回报的类别。
有了前几点,第三个因素就是管理人的选择,到底是in-house还是外包去做资产配置,两类模型海外都能见到,也都能做得很好。
从目前我们国内高校教育基金的发展阶段看,现在可能还属于婴儿期。我们2016年正式出台慈善法,很多一流大学的基金规模也非常小。但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校友捐赠的规模也开始大幅提升,我们又是教育大国,没有理由我们的校友捐赠基金不会发展起来。
而在未来的资金使用、资产配置上,我想大方向也会遵循相同的模式;不过我们的路径肯定是要针对我们的国情体系,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变化。
IIR创始人Emma:我们之前调研下来的感受是,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高校教育基金会、校友会,人员配置都非常少,没有专门的筹资团队,也没有激励机制。校友捐赠基金要想发展,核心还得体量先起来。您是北大校友,又是沃顿上海校友会主席,能否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在高校教育基金的筹资问题上,怎样才能打造一个更好的高校与校友间的互动关系?
叶庆:
我们熠美的大多顾委会成员也在海外大学的董事会上,对于捐赠基金的募集和管理的确有些经验和方法论。
首先还是刚才的结论,海外成熟大学基金会的筹资,都是覆盖校友数特别广、持续、高频、小额的捐赠模式。
从技术层面讲,校友互动其实不难,有很多的“tool box”
(工具箱)
,比如UPen和北大都有返校日、Class Gift、新项目的策划等等。
但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学校的重视程度和决心,以及人才的投入。
同样的预算、同样的资源,不同的人做效果会很不一样,关键还是结合本校特色反映出学校与校友的联结,赢得校友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捐赠的价值感。
大额捐赠更是如此,需要重点考虑捐赠人的需求,设计非常重要,这些工作不亚于咨询公司做的战略咨询。
另外,在筹资后的管理上,大学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平衡体系,我举英美各一个例子。UPen是很多学院可以独立筹资,最后统一放在学校endowment的大池子里去,各个学院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再去定分配、定配置,是一个社团的模式;牛津则更独立,各个学院独立核算,各自筹得的捐赠资金可以主动选择部分委托学校管理,有点类似我们的地方社保委托全国社保基金会管理资金。
资金的中央化管理,在投资方面的好处显而易见:你可以有更多的议价权,可以分散风险、安排各类对冲措施,头部的大学基金资金量大可以根据需求做单账户。
IIR创始人Emma:北大这次选择“委外”,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合作开展的契机和过程?
叶庆:
这些年作为校友,我们其实之前有过与北大基金会的交流,向他们介绍海外大学发展校友基金的一些经验,但实话讲,当时从未想过未来有一天能受托管理学校的部分教育基金。
这次与北大教育基金会能达成合作,最初我们也没有料到,但整个过程下来,我的感受是,北大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和准备。在做了大量研究并综合自身定位、战略和目标之后,他们做了委外的决定,要求找到理解大学长远发展目标、又能科学地设计配置策略、并有效执行下去的富有经验的专业机构。
而真正进入机构遴选的阶段后,是非常严谨的过程,基金会组织了严格的公开招投标,近40家机构层层遴选,熠美最终有幸入选,作为校友我们既感觉非常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IIR创始人Emma:不像清华和北大,目前绝大多数高校教育基金会的体量都非常小,也谈不上“配置”,“存在感”很弱。当前这种现状,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配置模式?
叶庆:
最近也有不少高校教育基金会的老师来找我们交流,我也在帮忙做些工作。
目前我感受到的首要问题是,很多基金会目前没有真正全职的投资团队,类似我这样的所谓“业内专家”、IC成员,可以义务给基金会帮忙,但即使这样算是有了一批外聘专家,也显而易见难以有长久专注度、稳定度。只有专注、稳定才能支持一个长久持续的策略,否则肯定会影响收益。
当然,基金规模普遍偏小也确实是一个制约因素
,但海外的大学捐赠基金的资产委托管理其实也有multi-endowment的模式,行之有效。Dietrich
(The Dietrich Foundation)
就很典型。
“标品”配置基金会可以自己管,而股权或另类资产这种很难做、又因为规模有限不好分散做组合的资产类别,可以委托给头部的大学基金会一起去管。
60分未满,100分很难,GP的筛选核心看价值创造
IIR创始人Emma:熠美接受北大委托的这部分资金,怎么做配置?
叶庆:
这是个专业工作,要考虑学校长远发展的诉求、捐赠的诉求、预算与现金流的要求等等问题,设计出一个科学的模型。
从整体的投资策略,到资产类别的配置,再到另类投资板块的配置,它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是不同类别、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一个组合。在这个整体框架下,我们再去挑选合适的GP。
IIR创始人Emma:刚才您也总结了好GP的共性,新GP的一些新特征,GP的筛选有什么标准,还会延续"FOF+直投"的模式吗?
叶庆:
对于GP的筛选,如果讨论评分表可能有点死板。定性的规则最多能到60分,60分要有,但60分之后,你要选90分、100分的好机构,其实很难。
核心我觉得GP团队还是要关注价值创造,勤奋聪明,有硬实力,还要与时俱进,更要不忘初心,能守得住底线。
"FoF+直投"的模式我们不会变,一方面这能提升整体回报,另一方面,它其实是一个补充整个资产配置灵活度的重要工具箱。我们核心团队都有直投经验,和“与我们关系较好的GP一起做好跟投”,一直是我们的一个sweet spot,而从赛道上讲,数字化目前是我们的大主线,数字化结合医疗、信息科技、智能制造、消费、新能源等,都是重点方向。
现实没有“理想国”,择“善”固执
IIR创始人Emma:熠美团队算是“国际视野+本土智慧”,您回国落地熠美后,参与并见证了人民币基金市场从混沌初开到渐趋成熟的演变。不论相较海外,还是内观自身,您怎么判断未来这个市场?
叶庆:
我们真属于顺势而为。
早期我们刚回国的时候,是纯美元,国内的私募股权领域只有外资活跃。像成思危成老发起的中国风投公司非常少,有也都是高层或央企支持下的小尝试。一直到07年合伙企业法完成修订、09年创业板开启,行业才迎来崛起,
这之后的十多年发展,我们总结有几个特点:十年100倍的急剧膨胀;急剧膨胀后带来的碎片化;此外,机构表现非常不稳定,业绩波动大。
市场里就这么多钱,大浪淘沙,必然是要分化、合并、关停并转,很多GP最后会消失,有一个合理的数量最终实现动态平衡,这是内生规律。
不过,现在市场往下走,也带来另一个secondary的市场机会。
以前secondary一直做不起来,是因为市场一直单边上扬,但现在,很多Special Situation可能都会起来。
另外,我一直呼吁人民币基金市场上出资人结构的多元化,现在,真正的专业化机构开始进场,社保、保险资金都在加大配置,CVC的崛起也一定是必然,大的基金会、家族,包括endowment,都非常新,虽然谁也没有水晶球去预测他们未来的占比如何,但我想他们都会扮演重要角色。
IIR创始人Emma:熠美是国内第一批探索受托管理人民币引导基金的专业机构之一,称得上是先锋,不过,似乎熠美也并没有因为这个“先行一步”,而站上国内引导基金爆发那几年的顶尖风口。为什么会这样?
叶庆:
我们2010年开始受托管理第一支上海闵行区的引导基金,我们受托管理的引导基金一期很早就达到 MM 3x,IRR 20%以上,可能受益于我们的专户管理理念,挡住了盲目扩张的诱惑,专注于给客户创造价值,才会有客户给我们的认可和支持,从一期到二期到三期一路加码。
风险回看的时候,都容易包装。
我们始终认为,长治久安的管理机制最重要。对于目前的引导基金市场来讲,我想未来几年是一个真正的压力测试。
IIR创始人Emma:这个行业,人才也是最重要的稀缺资源。我们注意到熠美去年与北大教育基金会也联合发起了一个实习生培养计划,回国10多年,现在您的人才观是怎样的?
叶庆:
还是举个例子,刚回国的时候,因为做美元出身嘛,我招人就喜欢specialist
(专业人士,专才)
,他们都把问题吃得透透的,理解足,人脉也足。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招聘和管理模式,可能反映在国情上还不成熟,比如Mid-Market Buyout(中型并购),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好交易机会?即使有了specialist,理想世界也还达不到。
国内现在还是个generalist(通才)为主流的环境,所以现在,我们只在一些非常细分的领域,比如早期的药物研发,才配specialist,其余大部分同事都算是generalist,大家不会只看一个赛道。
IIR创始人Emma:一直做“先锋”,一直要“突围”,会因为这样的妥协,或者说“因地制宜”而痛苦吗?现在的熠美一定和您当初回国时的设想不一样。
叶庆:
择“善”固执吧。
其实世界这么大,投资的领域这么广,市场变化又这么多,在这种环境下,真的就是要看准,吃透,然后还能守得住。
择善固执挺重要,但也很难,考验的是修为。